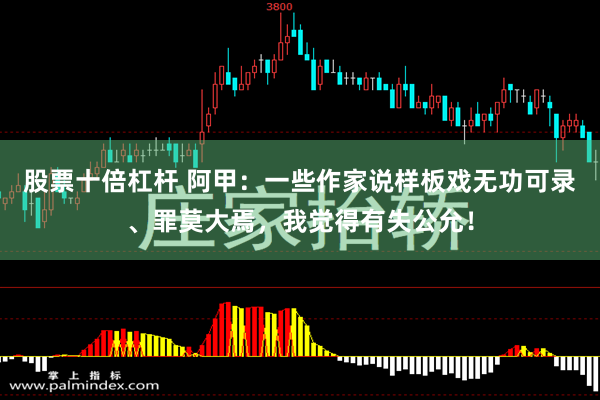
公告显示,截至2024年10月31日止一个月,华润置地及其附属公司实现总合同销售金额约人民币310.0亿元,总合同销售建筑面积约128.1万平方米股票十倍杠杆,分别按年增长12.4%及20.8%。
“样板戏”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先后孕育出三批杰出的作品,其体裁之丰富,涵盖了京剧、歌剧、话剧、芭蕾舞剧、钢琴伴唱曲、钢琴协奏曲以及现代交响乐等多种形式。其中,以京剧为体裁的作品尤为突出,共有22个精彩纷呈的剧目。
第一批“样板戏”中的京剧作品,包括脍炙人口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以及激昂壮烈的《奇袭白虎团》。这些作品以其深刻的主题、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第二批京剧“样板戏”同样不失为佳作,包括《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平原作战》和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娘子军》。此外,还有七个剧目在文革结束前处于修改阶段,如《红云岗》、《审椅子》、《战海浪》、《津江渡》、《草原兄妹》和《夜渡》,这些作品虽未最终定稿,但已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展开剩余90%至于第三批京剧“样板戏”,包括《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和《警钟长鸣》等五个剧目。然而,遗憾的是,这五个剧目因受到各种历史原因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登上舞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样板戏”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深厚的艺术传统作为蓝本参照。在京剧四大名旦崭露头角之前,京剧的舞台主要被老生戏所占据。谭鑫培对老生唱腔的革新,为京剧奠定了板腔音乐体系的基础。随后的四大名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京剧的风格化和个性化表达。
其中,程砚秋的贡献尤为显著。他在唱念做打、舞台设计以及导演体制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程砚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戏的局限,将创作的重心转向展现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这一转变使他更加注重按字行腔的创作方法,即强调腔调要紧密贴合唱词,而非机械地在固定的板式框架内填词。
自板腔体系建立以来,按字行腔已经成为戏曲音乐创作的基本法则。程砚秋的这一改革,不仅丰富了京剧的艺术表现力,也为后来的“样板戏”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借鉴和蓝本。因此,“样板戏”的革命并非无本之木,而是根植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新程式”的诞生,根植于一种特殊的风格,这种风格是经过长期的革命锻炼而形成的。这种风格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对群众深沉的爱和对敌人坚决的恨。阿甲在1958年提出了这一观点,并在随后的艺术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和发展。
作为中国京剧院的总导演,阿甲于1963年开始着手创作《红灯记》。他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自评《红灯记》时指出,该剧在运用京剧特点和表现现代生活矛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一评价揭示了《红灯记》成功的关键:它成功地保留了京剧的艺术特征,即“京剧姓京”。
然而,《红灯记》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与传统剧目中展现的“古代生活”相比,在真实性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同样,作为“战士风格”的体现,李玉和、李铁梅等人物形象之所以受到赞誉,主要是因为他们作为京剧人物,或者说是京剧化了的“英雄人物”,在表现上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与穿盔戴甲的角色相比,更贴近京剧的艺术风格,而不是简单地剥去了脸谱的性格。
“程式的表现方法”或京剧的美学精神,决定了“新程式”主要体现在外表(如服饰、扮相)和举止(唱念做打)等与时间地域相关的人为符号上,由普遍意义上的古代风格转换为革命年代的现代风格。
但无论如何变化,“新程式”仍然是程式的一种,它依照新的规则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仍然是特定观念的人格化。因此,在欣赏《红灯记》等现代京剧作品时,我们既要看到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也要理解这种创新是如何在保持京剧传统特征的基础上实现的。
不同的节奏能够传达出不同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又映射出人物内心的复杂心理。传统京剧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深厚的艺术底蕴在于它精准地展现了古代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它讲究含蓄之美,无论是青衣女子的微笑不露齿,还是男子行走时的方字步,都透露出古代人的端庄与雅致。通过水袖、髯口、翎子、靠旗等精妙的技术表演,传统京剧能够细腻地展现人物的情绪变化。
相比之下,“样板戏”则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风貌。它致力于塑造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以现代人的服饰和生活为背景,展现了现代社会的风貌。在传统京剧中,那些曾用来表现人物情绪、可进行延伸性表演的物件,在“样板戏”中因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失去了原有的用武之地。然而,话剧的一些表现方法却为“样板戏”提供了新的艺术灵感。
在节奏处理上,“样板戏”更加注重人物内心的心理节奏展现。它不再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动作和表情,而是深入人物内心,揭示其复杂多变的情感世界。在火热的革命激情的推动下,“样板戏”中的人物动作刚健有力,豪情万丈,这种外在的表现与人物内心蓬勃向上的情感相互呼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张力。
“样板戏”虽然与传统京剧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差异,但它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功地展现了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状态,成为了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这两部经典作品,深刻揭示了贫苦农民与地主劣绅之间的尖锐矛盾,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北方农村的生活画卷。
在《白毛女》中,杨白劳与喜儿的悲惨遭遇令人痛心。杨白劳为了躲债刚回到家,本想与女儿喜儿欢欢喜喜地过个年,却因买不起别的装饰物,只能给喜儿扯二尺红头绳。然而,地主黄世仁的突然造访打破了这难得的温馨时光。黄世仁以逼债为名,强抢喜儿,杨白劳奋起反抗却惨遭毒打致死。邻居们虽试图阻止,但在黄世仁的枪口威胁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喜儿被抓走后,在黄家受尽折磨,过着非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生动地反映了战争时期北方农村的社会现实。地主们霸占土地、私吞庄稼、逼收田租、放高利贷,导致农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钱、没有土地、没有庄稼、没有粮食。无数像喜儿这样的年轻女子被掠走做奴隶,受尽凌辱;无数男子被强制拉去做长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然而,随着火焰烧到每一个角落,穷苦人们终于迎来了翻身做主人的时刻。他们勇敢地站起来,与地主进行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农民与地主之间千百年来的矛盾也在这场革命中得到了解决,化作了滚滚长流注入了历史的深渊。
构成“样板戏”深层结构的核心要素是两大意象。这些意象,即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作品中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艺术典型是从万千中抽取出的最具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谈吐等的综合体现。在“样板戏”中,这些人物形象在高度警戒的语境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意象化,成为了具有深刻内涵的符号。
这些意象不仅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还通过具体的戏剧冲突和情节发展,展现了两者间的斗争。无论是正面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还是反面人物的丑恶嘴脸,都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和细腻的情节描写得以展现。
“样板戏”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其在塑造正面或英雄人物时,确实采用了将这些人物置于画面或舞台中心、前景的手法。这种处理方式旨在突出英雄人物的主导地位,展现他们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
在《沙家浜》中,英雄人物被始终置于前景或画面的视点中心,确保观众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他们身上。即使在敌我双方同时股票十倍杠杆出现的画面中,英雄人物也被安排在画面的前景或视点的中心,而敌人则被推至画面的边侧或后景。这种构图技巧不仅突出了英雄人物的主导地位,还通过视觉上的对比,强化了“我高敌低,我大敌小”的效果,体现了对敌人的全面击退。
《智取威虎山》在拍摄过程中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例如,在拍摄杨子荣只身打入匪窟这场戏时,制作团队最初设计了两个方案,但这两个方案都产生了“正不压邪”的效果。最终采用的拍摄方法是在展现威虎厅全貌后,迅速将镜头转向随着强光闪进画面的杨子荣,紧接着跳成特写,细致表现他藐视群匪、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这种处理方式有意省略了众匪张牙舞爪的凶相镜头,从而更加突出杨子荣的英雄形象。
通过这些具体的拍摄手法和技巧,“样板戏”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鲜活、立体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畏的英雄气概,还通过舞台和画面的巧妙设计,使观众在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感。这种处理方式不仅符合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也体现了文艺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传达价值观念方面的独特功能。
在讨论“三突出”概念的生成时,确实需要回溯到“英雄人物”这一概念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从延安时代开始,“工农兵”和“正面人物”等概念就在文艺作品中广泛流行,这些概念代表了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取向。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些概念逐渐被“英雄人物”这一术语所取代,成为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主题。
在建国初期,文艺界就开始强调表现新英雄人物的重要性。例如,时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创作的方向”。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认同,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1952年的报纸也大力宣传这一创作主张,进一步推动了新英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的塑造和传播。到了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正式提出“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并将其视为“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这一提法进一步确立了新英雄人物在文艺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创造新英雄人物还可以扩大文艺的表现领域,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旧社会的新的人民文艺。这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和经历,往往与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反映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奋斗和牺牲。因此,通过塑造这些英雄人物,可以更好地展现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彰显人民的主体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样板戏”研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深入探索后,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相较于新世纪之前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样板戏”研究展现出了诸多变化与发展,无论在研究氛围、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呈现出更为开放、多元和深入的态势。因此阿甲曾说:“样板戏脱胎于京剧又自成一派,对艺术有功,一些作家说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我觉得偏激了。”
在新世纪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中,研究者们对“样板戏”的可挖掘内容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致考查。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分析或历史背景探讨,而是将“样板戏”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社会背景中进行综合考量。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样板戏”研究更加立体、全面。
同时,一批起到引领作用的学者在“样板戏”研究领域作出了连续性的贡献。他们不仅深入挖掘了“样板戏”的艺术价值,还对其所反映的时代语境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样板戏”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
发布于:天津市



